
小岗村包产到户带头人之一严俊昌口述: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 |
|
严俊昌/口述 沈葵 徐小满/采访 徐小满/整理
编者按: “我们分田到户,每户户主签字盖章,如以后能干,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,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。如不成,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,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。”1978年11月24日,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吃饱饭活下去,摸黑集聚村西头一间茅草屋,按下红手印,秘密签订上述内容的“大包干”协议。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的宣言,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,改变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命运。40年来,有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”之称的小岗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回首往事,作为当年小岗村的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仍是感慨万千。本刊特选刊其口述《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》一文,重温敢想敢干勇于实践的“小岗精神”。 据悉,此文已收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、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《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——安徽凤阳、肥西农村改革亲历者口述史》一书(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),即将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。
我这个生产队长的头号任务:让小岗村百口人填饱肚子
回忆当年的经历,我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,群众基本上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,没有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。但是从1958年“大跃进”以后,群众的生活被破坏了,政府的大好形势也被破坏了,到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。三年困难时期小岗上饿死了67人,死绝了6户。我当时才十八九岁,我没有饿死掉,可以说什么都吃过的,那真是从死人窝里爬出来的。1961年以后,因为饿死了很多人,就解散了过去“大呼隆”的集体生产劳动形式。人都饿死掉了,还一天到晚搞假大空,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大锅饭不能再吃了。当时有个妇女,她家丈夫、孩子都饿死掉了,她怨天、怨地、怨我们的党的干部,她说我们家男人、孩子饿死掉了,干部家的老婆怎么还能生孩子呢?她恨得说,我如果有能力,我把干部家的孩子肉割来炒着吃。我(听到她说的这些话)头皮都麻了。我说天啊,一个女同志为什么能恨到这种程度?我哪天如果能当上干部,我要死在群众的前面。干部搞特殊,没有死掉,活着他会受到人民的痛恨,这是一种阶级恨。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,有人给我介绍对象,我根本不答应。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,我还要处什么对象。 1961年我成家了,我家属她确实可怜,兄弟姊妹都饿死了。我当时跟她说我不能和你成家,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,你跟我在一起早晚还是会饿死的。她说,天下老鸹一般黑,我跟哪个在一起不挨饿呢?我有了丈夫,我就有了依靠。我能够死在丈夫面前,我就知足了。我一听她说得这么惨,我不能再拒绝了。她搬过来,到我这一件衣裳都没有。那时候一人才发三尺布票,吃饭要粮票,穿衣要布票。有一次我老婆饿得在家直接瘫掉了,我马上抓了一把面,放点水搁锅里搅搅,搅点面糊子,喂她喝了下去,过了一会她爬起来了。 毛泽东说过只有落后的干部,没有落后的群众。那时候小岗生产队为什么干不好?关键是“大呼隆”的集体生产形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。因为在这种生产形式下勤劳人受打击,懒汉受表扬。为什么懒汉受表扬呢?小岗上年年不断有工作组来,但是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?来抓形式,搞一些形象工程。我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,我当干部,坚决不搞特殊化。因为我不愿意搞特殊化,所以我后来不当生产队干部了。 1977年底,庄稼还没收完的时候,梨园公社有人找到我,问哪个是严俊昌?我说:我又不是干部你找我有什么事?他说小岗这一两年的生产还是不行,担子你还要担起来,我们了解了,你当干部不搞特殊化,你又不能去要饭,那还不给你饿死了,你这次再干两年(生产队长),你全家的生活,我们公社包了。我说我要当生产队长,我就不要你包,换句话说,我要你包我全家的生活,我吃饱了,我挨群众骂。我不要公社给的任何特殊待遇。
详情请关注《世纪》杂志官方公众号: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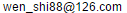

版权所有:上海市文史研究馆
 沪公网安备:31010102003435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:3100000112
沪公网安备:31010102003435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:3100000112
